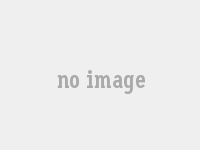戏曲改编是戏曲创作的一种方式、一种补充,是戏曲传承和发展的一条通道,凡是流传的剧目,大都是通过改编得来的。改编(修改)剧目比例大小,除了作者鉴于对戏曲本体、戏曲舞台、剧种特点和对表演的熟悉程度和理解层面以外,还要由导演通过与创演者的磨合、与时代的碰撞、与观众的沟通共同来决定。
戏曲艺术不是个人创作,戏曲艺术的创作者是一个团体,而且是以演出谋求生存发展的团体,编剧除了自己创作,还要依据剧团的特定条件来改编,才能满足剧团和观众的需求。不管什么时代、什么时候,对其所阐释的思想内容或提出问题的理解是如何正确,在之后的时代里也一定会有新的和更正确的意见。任何时代,任何时候,都不会把一切见解说完。对过去说过的总会有新的话要说,这也是改编的一个缘故。
改编给改编者提出了两个新的要求:一是需要说时代的新话;二是需要用新的艺术形式来说话。改编者调动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才能,使改编后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能获得新的艺术价值和新的艺术生命;使改编后的作品不但能长存戏曲艺术之林,还能和原著各领风骚。
我曾把任珍凡先生的文学本《魂断洪山》改编为上党落子《情系洪山》。在改编其故事情节、人物关系及文本思想的同时,在形式上着重以上党落子为外壳,以任珍凡文学剧本为内核,把《情系洪山》以上党落子的形式搬上舞台。除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再创作,我还改变了原著的结构和结局,改编了人物关系,也充实了人物思想,将这个文学本舞台化、戏曲化、上党化。
文学本《魂断洪山》主题突出,但结构比较松散;故事有趣,但节奏比较迟缓;人物典型,但关系比较单一;唱念顺畅,但台词比较繁冗。面对上党落子的观众和潞城剧团当时的演职员阵容,改编后的《情系洪山》,结构比较严谨,节奏比较明快,关系比较紧密,唱念比较精炼,深得观众喜爱。于是,我大胆删去“序幕”和第三场“子夜惊梦”整整一场半戏,还删去了郑玉莲、少女和歹徒三个人物,把第六场“丹心化险”和第七场“洪山忠魂”简练为一场戏,增加了一个“谢幕”的尾声。经过一番布局后,戏一开场很快就介绍完人物、铺垫完事件,埋伏下矛盾,马上进入了冲突。为使这部比较传统概念化的故事具有时代特点,我还刻意改变了故事的结局。因为我认为:主人公“倒下”之后,倔爷爷等“遗憾”的叙说、“忏悔”的表达有点画蛇添足。把倔爷爷送牌匾和“谢幕”简练合为一体,显得不拖泥带水,干净利索,收到了预期效果。改编后,原著中用暗示手法存在的“梦”,变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“梦”的形象或梦幻中的人物粉墨登场;两个月牙同时出现,时明时暗,时合时分,集抽象与具象于一体。它发挥了戏曲的写意性、虚拟性、程式性、符号性,以及综合电影、电视、话剧、歌舞、杂技、曲艺等多种艺术的审美特点,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表现主义、象征主义及荒诞手法的有机结合。
《情系洪山》在参加长治市新创作剧目汇演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同,获得了剧本、导演、舞美、表演、综合治理等各类奖项。每每演出,观众时而掌声不断,时而欢呼声迭起,时而泪流满面——创演者快乐极了,观众兴奋极了,我作为改编者和导演同样感到非常快乐。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的理念和自信:戏曲演出必须在继承基础上创新,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,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生命力。戏曲永远是在改编中传承。传统演出剧目拿到今天舞台上来演必须要经过改编;文学剧本拿到舞台上来演必须要经过改编;此剧种剧目移到彼剧种来演也必须要经过改编。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,也是观众殷切的期待。在戏曲发展进程中,我们要不忘传承,坚持改编,努力再创作!
改编不能心存杂念,顾虑重重,改编不仅是个人的再创作,更是集体的再创作,不仅要体现艺术个性,更要依靠集体的智慧,大胆创造,狠下再造之力。作为创演者,我们要坚持不断提升自身的历史修养、文化修养,不断完善自己的综合艺术创造能力,积极应对今后戏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,为新时代新演员、新创演者的茁壮成长,尽自己微薄之力,做出应有的贡献。